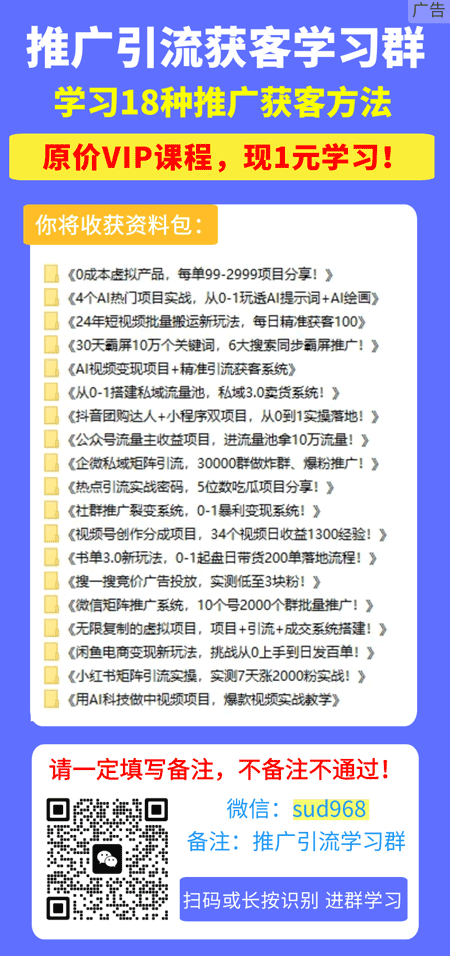人到了这个地步,都变得极端敏感,我刚一冒出那想法,就急得几乎哭出来,好像事情已经变成了现实一样。然而之后的情况更是急转直下,身旁的支架又开始不安分地“咯咯吱吱”响起来,从头顶流下来的土,“呼啦啦”灌了我一脖子。这一段金硐,似乎也要塌了。
骤然间的变化,在黑暗里挤压着大脑。我当时已经基本崩溃了,只会抱头蜷缩在地上,不知道跑也不知道动(事实上也无处可跑),心说这百八十斤恐怕就要扔到这儿了。那种等着被活埋的感觉,我至今难忘,特别残忍,真还不如让车一下撞死痛快。
当然,既然我现在能在这里诉说那时的经过,就说明我并没有死。金硐晃动了一会儿后,又慢慢平息了下来。上头不再掉渣了,我又听到了外边工具掘进的声音,频率比之前快了许多,看样子他们也察觉到了危险,加紧了进度。
大约半个钟头之后(这是事后他们告诉我的,我当时已经没有这种概念了,只能说度秒如年),身边的硐壁突然“扑哧”一下,被捅透了个窟窿,另一边马上响起兴奋的喊声,说通了通了,又开始叫我的名字。
一丝久违的微光散进来,把我眼睛刺了一下。他们当时叫我,我可能应了一声,也可能没应,主要是脑子一片混沌,朦朦胧胧已经有点儿分不清真实和幻觉的区别了。只记得洞口被很快扩大后,一个人探进来了半个身子,然后两手叉起我胳肢窝,拖拖拉拉地把我弄了出去。
外边的阳光还很强烈,我眼睛一时不适应,看不到东西,只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人影。人也变得有些呆,搞不清方位也走不稳,只能捂脸瘫在地上,听凭他们喂水擦脸,推拿顺气,好一番伺候。
我终于能睁开眼了,重新看见了天空,发现它那么蓝那么好看。这时终于恢复了点儿思维,我立马一个激灵坐起来,指着金硐有点儿口齿不清地急喊,说快快,里头还有个人,快抓出来别叫跑了。他们几个不知道刚才的事,都是一愣,不过武建超很快把那家伙从里头拽了出来,证实了我的说法。
他们几个一看突然冒出了个从没见过的人,全跑了过去看新鲜。我也跟着爬了过去,把前因后果一说,他们也是议论纷纷,围着那野家伙就研究起来。
那人赤身裸体披了张兽皮,怪模怪样的,一脸大胡子遮住相貌,更看不出什么来路。大家都在啧啧奇怪,但似乎只有王老爷子不关心。他一人站在边上,冲着我们一脸焦急地说:“行了行了,人也救出来了。有啥稀罕的回头再说,咱先找赵胜利去吧!”
“老东西,你还有脸催!”武建超回头骂了老爷子一句。我不明白他俩这话啥意思,左右一看,这才发现赵胜利竟然不在,忙问:“赵胜利怎么了?”
他们三人一时沉默。武建超走到一边儿拾起枪,掰开看了眼子弹,头也不抬地告诉我:“那小子跑了。”
我微微吃了一惊,问什么时候跑的?武建超说就刚才。
我还想问个明白,他却没工夫搭理我了,开始手脚麻利地收拾东西,把别着子弹的皮带扣在腰上,又带了一壶水,一拍阿廖沙说:“望远镜借我使使。”说完根本没等对方点头同意,背着枪转身就走。
阿廖沙有个62式军用望远镜,我们之前在营地里看见过,只不过因为过了闪电,外边的铸铁壳子被烧熔了一半。武建超借这东西,估计是待会儿找人要用。
我现在这个状况,就算想帮忙也有心无力。王老爷子本来在边上急得跳脚,一直催快点儿快点儿,这时看武建超走了,也跟了上去。但武建超似乎很恼他,转身一脚,“啪叽”把他跺翻在了地上。
我一看武建超竟动了粗,霍地站了起来,大声问这是干什么?可他根本不睬我,而是指着老爷子恶狠狠骂道:“你他妈的哪儿也别想去,安生待着,回来再跟你算账!”说完就离开了。
老爷子被这么一踹,痛得半天爬不起来,只能冲着武建超远去的背影大骂,脏话土话一大串,也听不清到底说的什么。我当时完全摸不着头脑,只能晃悠悠走过去,蹲下来,稍稍用力抠住他的肩膀,硬着口气问道:“老爷子,到底怎么回事,你给我说清楚。”
还没等老爷子回答,阿廖沙却跑过来拉着我问:“大学生,你是让那人抓到硐里去的,对吧?”他指着躺在地上的野人,我也点了点头。他看着我,脸色却急切起来:“我那个‘情况’可能也被掳到里边了,咱得进去找找。”
我让阿廖沙先别慌,要救人也得把情况问清楚再说。那野人自从被拉出来后,被我们绑得动弹不得,也很安静。我问了他几句话,可他好像又听不懂了,或者说根本没有听,只会冲着我们龇牙咧嘴地示威,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声音,就跟个被抓住的动物一样,神态很野蛮。
“别问了,这是个怪物,不会人话。”阿廖沙只关心自己的“情况”,语气还是很着急。他的推测其实合情合理,雷击之后那女人不可能凭空消失,结合我的遭遇,唯一的解释就是被眼前这家伙掠走了。但阿廖沙要进金硐去找,我却不敢立刻同意,只是告诉他硐里那头也被堵了,想找人就得继续往深处挖,恐怕还要费大功夫。
阿廖沙显然没听出我的潜台词,说无论如何也得进去看看,也不再管我怎么说,拾起铁锹又钻回了金硐。其实刚才那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,他们几个不顾安危把我救出来,现在需要我去救别人时,我竟然因为可能有危险而退缩,实在很不仗义。
然而,就在我鄙夷自己的言行,打算和杨要武一起跟上帮忙的时候,眼前的半条山坡又突然微微一陷,大山就像在咳嗽似的,轰轰然从矿井出口喷出一大团黄烟,地面跟着颤了起来。这情况不用说都明白,金硐终究是没支撑住,又塌了。
我心说这下糟了,拽上老爷子,和杨要武抢上就打算挖人。不过谢天谢地,还没等我们到跟前,阿廖沙就从硐口的烟团里冲了出来。他一边咳嗽一边朝外跑,拍着身上的土,气急败坏地把铁锹往地上一扔,“呸呸”吐了几口唾沫,叽里咕噜骂起了俄国话。
我被埋进去时还是早上,如今已经过了中午,鸡飞狗跳了大半天,几个人一个个灰头土脸跟西安兵马俑似的,不过好在没出什么大事。阿廖沙还想找他的小姘头,但金硐垮成这个样子,一时半会儿怕是挖不开了,只能从长计议。他有气没处撒,就逮着那个野人揍了一顿,又是踢又是捶,把那家伙打得哇哇直叫。我赶紧拦着,说你打他干什么,打死了啥都问不出来了。
阿廖沙气哼哼地说:“你看那样子,能问出个屁!”我叹了口气,把他挡在一边,给那野人收拾起骨折的胳膊。眼下太复杂的处理也做不了,只能给胳膊简单复原位置,里边垫了层软衣服,上了点儿药,找树枝做了个夹板绑好固定。我手上干着,心里却在苦笑,自己还真成“大夫”了,医人又医畜,还得会接骨正骨。
那野人见我给他治病,倒也不抗拒,就是态度依旧很不友好,有次我凑得近了点儿,他竟一下勾起头张嘴就咬,吓得我赶紧把手抽了回来,心说这人完全不懂好歹,到底哪来的?难道是山里的原始民族,就跟非洲那些藏在丛林里没开化的土著人一样?但很快,我无意中注意到了他的牙,就马上否定了自己的想法。
我让阿廖沙帮忙,顾不得那野人的强烈挣扎,捏着他下巴,撬开了他的嘴。往里仔细一瞅,他上下两排牙的牙根和齿缝,都透着一种深棕色的痕迹,而牙齿的内侧更是黄得发黑。我顾不得那人嘴里的怪味道,伸手指给阿廖沙看,说这是明显的烟垢,只有常年吸烟的人,才会把牙熏成这个样子。而烟渍这种东西,只要沾到了牙上,你一辈子都要带着,刷牙都刷不掉(当然,现在有那种超声洗牙机,就另当别论了)。
这里无须多做解释,阿廖沙也明白我什么意思了。我们几个除了武建超,都是吸烟的人,深知烟垢的顽固,只不过大家贪图一时快活,不在乎这些形象问题罢了。这人牙上有烟渍,就说明他肯定曾长期吸烟。虽然我不知道古代人接触烟草的确切年代,但几乎可以肯定,地上躺着的这家伙,十有八九不是什么土生土长的野人。杨要武和老爷子再次凑了过来。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,想通这一点后,我再观察那人时,就觉得他的混浊发灰的眼珠里,似乎也不全是野性难驯,好像多少还带着些未泯的人性和良知,他之前能听懂我说话的事,这样也能解释通了。
从脸上的胡子和皱纹来看,这人显得很老,但也推测不出他到底多大年纪。这么深的山,不是常人来的地方,我们猜要么是流落到这里的牧民、蜂农或者通缉犯(西部地区地广人稀,靠近边境,还容易搞到枪械,所以很多外地逃犯往口外跑),要么和我们一样是来淘金的,甚至说是当年金场遗留的人员也不是没可能。只是不知道他究竟经历了什么,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?
困在金硐里时我就想过,这里的很多蹊跷问题,估计都要在这人身上找答案。然而我尝试着跟他交流,他却只会咧嘴到处乱瞧,咿呀怪叫,愣是一言不发。对这号人,你就是上刑恐怕都不管用,我们一时彻底没辙,让人很是沮丧。
这头儿毫无进展,我的注意力又转了回来,想起了刚才的事,就扯住老爷子:“你还没说呢,赵胜利怎么就跑了?”
只能说,一切都和金子有关。
老爷子当时有些支吾,并没直接讲,而是把我拉到一边,避开了阿廖沙和杨要武,这才说起刚才的经过。
当时我被埋了进去,武建超把他和赵胜利喊过来帮忙。几个人收拾工具一分配,弯腰跪着轮流下硐,每人几米的朝前挖,后边的人往外运土,另外又砍些小树回来当支架,好边挖边支护,防范硐子再垮(也幸亏这么撑住了出口那一段,阿廖沙才没被埋进去)。
就这样干了好几个钟头,他们绕开塌冒的地段,从旁边打出了一条半米宽、将近十米长的通道,估算着不久就能挖到人了,更加快了进度。然而就在胜利在望的时候,不知谁提醒了一声,他们这才突然意识到,去附近林子砍树的赵胜利,已经好长时间没回来了。
莫名其妙地又丢了个人,几个人都有些慌了,手上的活儿也停了下来,商量说到底怎么回事?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有段时间,我在里边没听到他们的挖掘声。
当时几个人里只有老爷子知道底细,他发觉赵胜利不见了之后,立马捶胸顿足,直骂自己太大意了,让大家赶紧去追人。几个人一逼问,他这才说赵胜利并不是丢了,而是趁着别人忙乱的当口,卷着金子自己逃了。
阿廖沙他俩和我们不是一伙的,都懂规矩,一听是金子的事情,就马上闭嘴不再多问。而老爷子说一半留一半,武建超依旧不清楚那小子到底为啥要跑。老爷子催得虽然紧,而且这种节骨眼上,有点儿良心的人都不能把还埋在山肚子里的我扔下,转身去追赵胜利,所以短暂的停顿后,他还是选择留下继续救人。
老爷子看武建超竟动也不动,急得直蹦,恨不得自己去追,不过他很清楚自己身体不行了,就算撵得上,也肯定拦不住身强力壮的赵胜利。无奈之下只能钻进硐,一边帮武建超往后运土,一边把前后的原委说了个清楚,好让他明白事情的严重,赶紧去把赵胜利找回来。不过巧的是,他这边刚断断续续说完,那边武建超就把金硐打通了。
至于赵胜利跑掉的原因,则需要从好几天前说起。
首先是昨天下午,当时我和武建超正在山上跟哈熊拼命,老爷子和赵胜利还留在山下湖边,这本来没什么,但之后下起了大雨,赵胜利就变得不正常起来。
他先是一个劲儿地望天,自言自语地问这雨什么时候能停。而随着雨越下越凶,人也越来越坐不住,就跟憋了泡屎找不到茅房似的,在原地团团乱转,时不时看眼外边,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。老爷子问他到底着急什么,他却又什么都不说。就这么持续了十几分钟,赵胜利就跟终于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,竟一个招呼都没打,突然抬脚冲出了屋子。
那会儿下得正紧,赵胜利一头扎进水幕,转眼就不见了。老爷子心里奇怪,在后边叫了一声没反应,咬咬牙也跟了出去。追着那小子一路跑到小河那里,从远处见他在河边转了几圈,像是选了个地方,然后就“扑通”跳了下去,浮浮沉沉地开始在水里边乱摸。
雨很大,小河也跟着涨了不少,人这时候下水很危险。老爷子看赵胜利像是在找什么东西,就跑过去问。赵胜利没想到他会跟来,明显的一阵紧张,最后才不得不坦白,说他是在找自己藏的金子。
听到这里时,我还没察觉什么太大的问题,只是纳闷怎么能把金子放在水里?老爷子一解释我才了然,说原来好多天前,赵胜利有次在那小河里捞菱角吃,无意中发现了水下的河岸上,藏着个比胳膊粗的土洞。他趴下用手一掏,一半湿一半干摸不到头,于是就突发奇想,把那儿当作了自己放金子的地方。那位置倒是真的很隐蔽,只可惜他没考虑周全,所以天一下雨就着急了,因为担心涨水会把洞里的金子冲走。
这附近生活的有河狸,大哥曾说它们会打洞做巢,我心说难道赵胜利在水下发现的洞子,是人家河狸的家门口?在那里藏金子,也亏他想得出来。不过如今回头再看,我却只能感叹赵胜利太自作聪明,假如那时他没有多此一举,他后来结局也不至于那么惨。
不过在当时,我只觉得老爷子绕了一大圈,还是没讲到关键地方,就叫他少啰唆没用的,赶紧说赵胜利为啥要跑。而他咳嗽了一阵后,只往下多说了一句话,我就彻底明白了。
新来的朋友请别忘了点赞收藏啦,方便查看更新
好了,这篇文章的内容发货联盟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,如果大家网络推广引流创业感兴趣,可以添加微信:80709525 备注:发货联盟引流学习; 我拉你进直播课程学习群,每周135晚上都是有实战干货的推广引流技术课程免费分享!